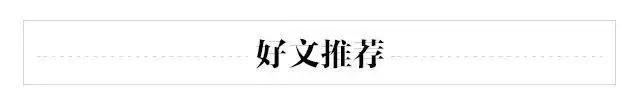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一次次出发,是为了更好地抵达
作者简介:第18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得者。现任辽宁报刊传媒集团(辽宁日报社)北国融媒体中心副主任、新媒体创意和制作编辑部主编,文学硕士,高级编辑(二级)。从事新闻工作29年,擅长新闻评论、深度报道写作,承担辽宁日报10余个重大主题报道的策划、责任编辑和主笔。新闻作品8次获得中国新闻奖。
今年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第二十九个年头。我始终觉得,新闻给予我的远比我给予新闻的多得多……
任何一个职业,只有单方面不断付出,是很难持久的;只是打工心态的等价交换,早晚会失衡。最好的状态是双向奔赴,我们交出了好的产品,并从中获得成就感,同时职业经历也让我们获得成长,生命越来越丰盈。
新闻之于我,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职业。我很感谢20多岁的自己选择了做新闻。
一次次采访经历坚定了我的新闻初心
新闻的魅力是多元且独特的:一方面,它每天都是新的,其蕴含的创造性与挑战性,凌驾于诸多行业之上,从业者欲求卓越,唯有持续学习、雕琢自我;另一方面,新闻宛如一把钥匙,悄然开启我们认知世界的新大门,重塑着世界观与人生观。于我而言,一次次奔赴采访一线、伏案写作的过程,恰是坚守理想信念、雕琢内心、完善自我认知的逐梦之旅。
我也感恩每一位采访对象。有时候细想一下,能对一个陌生人敞开心扉,让你走进他的世界,给你讲述他的故事,是多么难能可贵!所以,我总是提醒自己要保持谦卑、保持敬畏,珍惜每一次与人交流的机会,感恩他们的分享。也正因为他们的无私,新闻才被赋予了温度,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方能走进千家万户。采访生涯之中遇见的很多人和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次,是采访一位乡长。1995年3月初,我还只是报社的实习生,所在的经济部策划了“3·15”消费者权益日专题,一位老师带着我下乡采访关于假种子的新闻。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雨夹雪的阴冷天,对村民的采访结束后,我们直接去了乡政府。乡政府是一排特别简陋的平房,已经到了下班时间,收发室的大爷一听我们是辽宁日报的记者,立即表示乡长还没走,直接将我们领到了他的办公室。当时,乡长坐在桌子后面,披着军大衣,手里拿着一本书在读,那本书的名字是《西行漫记》。
那是我第一次去农村,也是我人生中见过的第一位乡长。这种新鲜感一直延续至今……我时常在想,如果没有记者的身份,或许我对农村、农民的认识永远只能停留在游客层面。如果不是因为当记者,我也肯定不会遇见一位在潮湿简陋的乡政府办公室里披着军大衣读《西行漫记》的乡长。
第二次,是采访一位院长。1996年,我当记者的第一年,有机会跟随报社的前辈王功熹老师去采访。功熹老师是一位杂文家,行文老道辛辣,令我仰望。我们去黑山县采访县人民医院院长,一位医德、医术俱佳的医务工作者。采访结束,吃午饭的时候,这位院长很抱歉地跟功熹先生说:就不能陪您喝酒了,我们拿手术刀的,手不能抖啊。功熹先生听完,立刻回应:我们拿笔的,手也不能抖啊。
人生中经常是这样,看似平淡的一句话,会成为你的长久记忆。我很庆幸在我职业生涯的开始,就听到了这样的话。手抖,写不好字;心不正,做不好新闻。三国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有一句著名的话:“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以前觉得这句话离我很远,可就在那一瞬间,我才意识到,我手里的笔是这么有分量!用心为文,就是从功熹老师这句话开始的。
第三次,是采访一位校长。2000年,丹东凤城东方红小学校长包全杰去世,他的事迹很感人,省委书记批示要大力宣传。那次采访,报社派我去写长篇通讯,还在凤城遇到了已经退休的老前辈、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李宏林,他是去为包全杰写报告文学的。
因为是重大典型,县里列了长长的采访单子。光是座谈会就要开整整两天,参会的有东方红小学的老师、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几十人。座谈会之后,还要去学校和几个学生家里实地采访。一起采访的记者们都觉得素材早够了,可李宏林老师还是不断提出采访要求,还特别提出要去包全杰的墓地看一看。我还记得李老师手里拿着录音笔,每次向采访对象提出一个问题,就对着录音笔再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一遍,到了墓地,也对着录音笔录下他看到的每一个细节。李老师看到我们好奇的目光,自嘲地说:老了,记性不好了,眼睛也花了,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现在我也到了记性越来越不好、眼睛也变花了的年龄,我会经常想起李宏林老师采访的样子。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新闻记者是可以干到老的。可我们能不能像李宏林老师那样,在精力和体力都下降了之后,仍然保持着那份对职业的敬意、对新闻的热忱,对待每一次采访时仍然充满好奇、始终专注?
透过乡长、院长、校长的采访故事,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理想信念、价值观,以及对新闻事业的初心,都是由这些采访对象和新闻前辈共同塑造的。新闻的高度是由新闻名家、新闻名篇和一群有理想、有操守、有情怀的新闻人共同累积起来的。现在出去采访,听到别人介绍自己是“大记者”,我也会心慌:因为我总会想到那些新闻前辈,总会问自己,你达到他们的高度了吗?我想说还没有,所以还要更加努力。

作者(左六)在本溪满族自治县为小学生上历史公开课。
一次次采访,是为了抵达历史的深处、时代的高点、群众的心里
13年前,我做了一件在别人看来特别“离谱”的事:在做了几年的新闻部门主任后,我给报社领导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主任一职,重新做一名普通记者。大家都在议论:是工作没干好,还是在闹情绪?其实都不是,只是因为我发现手中的笔越来越“涩”了,文字越来越苍白,内心的恐惧一天比一天强烈:我怕自己有一天不会写了……
那一年,我41岁,重新出发!
这一次出发,我和我的团队走进了历史深处。怎样让遥远的历史与今天的现实联系起来,怎样让红色文化成为我们今天前行的动力?我们想要在大历史的褶皱里寻找鲜活的细节和更新的感动。
讲述其中的一个采访故事。抗战那一段历史在辽宁的百年红色文化中地位重要。辽宁是14年抗战的起点,“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伪满洲国成立。那时候的百姓走在大街上,都会被日伪警察拦住,如果说自己是中国人,是要被抓进监狱的,只能说自己是“满洲国人”。而大连,更加苦难深重,早在1905年就被日军占领了。我要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大连的莲花山,山上有很多日伪时期的废弃墓碑,那时候的大连,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大部分墓碑上使用的都是这样的纪年:昭和——日本的纪年,康德——伪满洲国的纪年。
但是,在荒草丛中,我们发现了一块特别的墓碑,墓主人的名字是赵程氏。赵程氏的去世年份是这样写的:民国二十三年,用的是中国的纪年。民国二十三年是1934年,那时候大连已经被日本占领29年了。赵程氏可能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国百姓,她或许没有能力成为抗日的战士,所能做的只是在死后用这样的方式证明自己是中国人,她将生命最后的定格留给了家国。站在墓碑前的那一刻,你会更加明白:何以为中国人!
我们也走进了大地的深处。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报社推出了系列策划《大地情书》。这是我记者生涯中最特别的一次采访,我们5组记者,选择了省内5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蹲点调研。当时报社领导给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不仅要写出小康社会的新图景,更要写出乡村群众的心灵成长史。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每个人都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时间。
一个多月的时间会产生什么变化呢?刚进村的时候,老乡们接受采访,通常会问这样三句话:“你让我咋说?”“我这么说行吗?”“我说的你敢写吗?”三句话里隐含的是同样的意思,他们不信任记者,不相信我们可以传递他们的心声。一个月之后,我认识了大半个村庄的人,大家都习惯了我每天举着自拍杆在村里走来走去,很多人说话的时候甚至忘了我是记者。其他几组记者也是如此:记者李越住在村妇女主任家,家里的男人进城打工去了,两个女人每天晚上躺在被窝里聊天,没出三天,每家的婆媳关系、邻里间的亲疏远近弄了个门儿清;记者李波住在村委会办公室里,正是玉米收获的季节,跟他一起住的是收庄稼的拖拉机手,李波白天同他们一起出工,晚上睡觉前一起喝酒聊天,越说越掏心掏肺……
我们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走进了他们的心里,于是,我们出发前做的那些功课,那些写在文件中的每一条政策、每一个术语,都变成了广袤田野里生动的乡村全面振兴实践。
我们完成的不仅是一次次采访任务,更是一次次有价值的生命体验。这一次次的出发,让我终于明白了:无论是我一直思虑的写作困境,还是新技术带给我们的挑战,其实真正担心的是身为新闻人的我们失去与时代、与土地、与人民的连接。我们的每一次出发,就源于这份恐惧;而我们每一次所要抵达的,就是历史的深处、时代的高点、群众的心里。

作者(右一)在铁岭市北关村采访。
勿忘黄土地,深嗅大地的芬芳、谛听人民的心跳、记录时代的华章
对新闻最大的感谢,是它让我对生活的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越来越充满感情。
我始终记得新闻名家范敬宜先生写于1993年的一篇作品《勿忘黄土地》。范敬宜是从我们辽宁日报走出去的著名记者,他曾经在辽西农村生活了近10年。20世纪80年代,已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先生接待了从辽西农村来的一对带着孩子进京看病的夫妻,孩子病很重,夫妻俩既没钱又投医无门,于是找到了他们在北京唯一认识的“大人物”老范。范敬宜不仅帮忙联系医院,还动员报社员工捐款,凑够了医药费。文章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每次读到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我都会泪湿眼眶:“我希望我们的同志,特别是青年同志,不要只看到王府井周围这一平方公里,要经常了解960万平方公里上的喜怒哀乐。不要只津津乐道8000多元一双的皮鞋、上万元一套的西服,要经常想到全国农民的每年平均收入还只有700多元。不要只为在歌榭舞厅一掷千金、万金的‘大款’们喝彩,而要经常想到还有多少终年辛勤劳动的人们,连12元一宿的床位都不敢问津。”今天的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勿忘黄土地,仍然应该是我们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初心——深嗅大地的芬芳,谛听人民的心跳,记录时代的华章。

作者(右)在铁岭市北关村采访。
现在有一句流行的话,叫“择一事,终一生”。选择了一个你喜爱的职业,用一生的时间把它做好,很幸福。而像我这样注定要在报社退休的“择一处,终一生”者,我觉得更幸福。或者说,选择一个事业然后终其一生,是一种幸福;而选择一个单位终其一生,则是一种幸运,它不仅需要一个人的努力,更需要这个单位所有人一起努力,朝着一个方向共同发力。
我很幸运,因为我有幸看到了无数这样的前辈,同时也看到了无数跟我一样甚至更加努力、更加辛苦的同事和同行。
祝愿年轻的记者朋友也都拥有这份幸福与幸运。
原文刊发于《新闻战线》2025年3月(上)